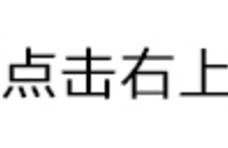近些年,全国人民好像在一件事儿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就是——“北京是美食荒漠”。对此,作为一位普通北京市民,我完全无意反驳,主要是无胆反驳。
后来,又看见一句话说“北京是平价美食沙漠”,我觉得这句话更客观,当然也更给北京人民面子。前些日子,跟闺蜜去天津玩了两天,吃了几顿饭,实话说,就天津那几顿饭,如果在北京,价格至少要乘以二——北京不是没有好吃的,只是贵。我总跟朋友们探讨,比如同样是一千块钱,北京只能吃仨好馆子,祖国其他地方可能能吃六个八个十个也许更多……
本人不是美食家,说不出那些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单纯就是馋,再加上自己不会做饭,这些年的饭也基本都是在“美食荒漠”的各色馆子里解决,准确地说,写这篇文章并不是想要聊“吃”,而是单纯地聊聊这些年在北京吃饭的一些经历和故事,都是个人体验和感受,您就当看看北京人民有多可怜,也行。
文 | 原版二姐
烤鸭
一说什么吃的能代表北京,大家都会想到烤鸭。在我小的时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烤鸭是尊贵的吃食。那时候大部分家庭都穷,吃不起。最早听说烤鸭,是听我妈说,我大姨夫“一人儿能吃半只烤鸭子”,大姨夫是大学教授,在女婿里头大概算是收入比较好的。那时候我没吃过也没见过烤鸭,只觉得那种吃食,很神秘。
上大学的时候,同班一个女同学说,地上捡了二百块钱,就跟男朋友去吃全聚德了。只不过没几天,她自己就丢了钱包,在那儿慨叹“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我心想,你不是前几天才捡了一只烤鸭么?
在北京说烤鸭,全聚德好像是跨不过去的坎儿,但我记不太清楚第一次吃全聚德是什么时候了——如果是美好的体验,它应该在记忆里留下痕迹。
大概是1996年还是1997年,一个客户请吃全聚德,在北图附近。客户是南方人,他大约觉得就俩人,点多了吃不完也是浪费,所以我们点的都是鸭心啊这类边角料,一共花了大概是168块钱。在那个年代,这是很贵的一顿饭了。还没吃到正主儿。我对这顿饭一直记忆深刻,因为每道菜上来都像是刚刚经历了火焰喷射器一样,焦黑焦黑的……后来有职业美食家同事说全聚德最好的那家店,是北京饭店二层那家,“甚好”。也有人说玉泉路店的火燎鸭心还不错。但我都没去过,无从判断。
2000年左右,我个人最爱的烤鸭店,是城西航天桥紫玉饭店一层那一家。店名具体叫什么都忘了,但坐标紫玉饭店是记得的。1999年春节前,我请三位女同事吃过一次,四个人吃了320,记得清楚首先也是因为贵啊。那个烤鸭,鸭皮是透明的,怎么形容那个颜色呢,不是焦糖色也不是枣红色更不是金黄色,它更像是这三种颜色调和出来的,泛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光。口感是韧而脆的,不是娇滴滴的脆,也不是老棺材瓤子那种gěn。从此烤鸭在我心里的标准,就是紫玉饭店的烤鸭。颜色浅一点深一点的我都觉得遗憾。
烤鸭的精髓在于皮,在不必分你我、装孙子的小圈子里,每次吃烤鸭,我都是拒绝鸭肉只吃鸭皮的,全然不顾总胆固醇指标早就爆了。能够放肆做自己,那是高端的幸福。
在北京,还有一个烤鸭店风靡过一段时间,叫鸭王。我请爸妈吃过,在海淀南路。别的都印象不深了,单记得我妈又开心又觉得贵,又能跟邻居吹牛说闺女请吃高级饭馆了又替我心疼钱。唉,妈妈……对爸妈来说,吃什么毫不重要,觉得闺女很孝顺,这比一切都重要。
后来就有了一大堆平价烤鸭店,大鸭梨、天外天,前门那边胡同里有个德高望重的叫什么来的,前几年路过过一次,利群烤鸭店,生意还挺好。
再然后,也就是最近这三五年,以烤鸭为招牌的北京菜突然就风起云涌了,遍地开花了,集体升级了。除去那些38一只烤鸭搅局的,想吃好吃的烤鸭,变得so easy了。
我家猫的兽医小哥哥,前年夏天家人来北京看他,他说家人说了,到了北京,烤鸭怎么也得吃一顿,问我有什么推荐,还说,“姐,一定要吃你们北京人吃的,不要给外地旅游的人吃的。”我给他推荐了大董、拾久、四季民福、京味斋还有那年新起的网红餐厅京华烟云,这几家是我亲自用嘴尝过才推荐的,也算丰俭由人了吧。当然如果离住的地方近,四世同堂、北平食府名声也不错。
小哥哥怯生生地问,“全聚德不推荐么?”
“我们北京人不吃全聚德!”关于全聚德,再多说一句,老字号餐饮品牌有它的不易,但全聚德做不好,别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顾客,连《天下第一楼》那话剧都对不起。
亲尝的那几家烤鸭,至于哪家最好吃,我跟懂吃会吃的闺蜜们意见不统一,我认为拾久的最好,她们认为还是四季民福的好。
说起来,四季民福真是人民的烤鸭店啊。前年,一个嫁到西班牙的妹子带夫家来北京旅游,说西班牙人民好奇烤鸭,让我们推荐,四季民福得票最高。就是四个人里面有三个推荐四季民福的。
我只吃过一次四季民福,吃得少主要是懒得排队。唯一一次吃还是路过,双井那个店,扭头一看不排队啊赶紧进去吧,下午四点二十就吃晚饭了。那一餐给我印象最深的,倒还不是菜有多么惊艳,真的谈不上惊艳,但是它不犯错啊,每一口都不惹你生气。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有个细节:鸭翅,是剔过了骨头的。这个细节收买了我。尽管我那么不喜欢它的装修。
关于北京的烤鸭,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大董。
大董,曾经是我认为的北京菜的天花板。多年前的某个冬天,我们部门团建,跑去吃了顿午饭,人均一百六七,但是谁都没吃饱。第一次在大董吃饱了,是一个以前的同事妹子从广州来北京出差,点名要吃。我们三个人吃的,吃没吃烤鸭不记得了,当时感动我的是一小碗炸酱面。就是一碗炸酱面,他可以做到那么精致。
最爱大董的那些年,实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去大董,也不用点什么横菜,给我一碗炸酱面就开心了。大董的烤鸭是后来才吃的。确实不错。但最近这几年,渐渐觉得去大董不知道吃什么了——想很家常地随便吃吃,变得越来越难。今年过年的时候,跟闺蜜去吃的北四环融科中心店,菜单一吨多重不说,每个菜都得罪人。也许是因为过年,各种跟不上,菜不是没味儿就是凉。替他们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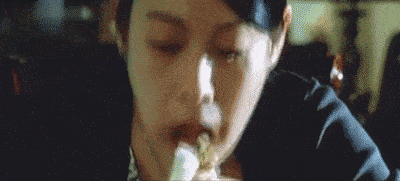
▲ 图 / 电影《天下无贼》
涮肉,烤白薯和稻香村
现在,我一年也吃不了一两次烤鸭,但是涮肉,还是比较常吃的。
说到涮肉,我纯个人的体验是——吃过聚宝源就不爱吃别人家的了。记得我第一次吃聚宝源,是后海店,当时只是觉得肉特别好,至于哪儿好哪儿不一样,同吃的人说,“涮了这么半天,没有血沫儿。”从此,老北京涮肉只要锅里出现血沫,在我这儿就是需要努力的——当然,这纯属个人爱好。
聚宝源常年排大队,听说牛街店尤其如此。牛街店我没去过,后海店去的次数比较多。假聚宝源也碰上过。那些店里,“聚宝源”三个大字招牌没有挂在楼外面,只挂在楼里大厅,看着就令人起疑,生怕谁知道似的。装修风格不一样,服务员也不一样,问啥都不知道。主要是,从凉菜到肉,品质是没法比的。
至于最完美的涮肉,还得是冬天,特别是初雪的时候,跟最好的朋友围着一个锅子,嚼着聊着,不必顾及个人形象地放肆吃,最好都别开车,可以喝两口。我不喜欢“仪式感”这个词,对我来说,初雪涮肉,不是什么仪式,它是一个节点:正式进入冬天了。可是这又很难,因为有可能一冬天都不下雪。那么退而求其次,只要下雪,就可以专程去吃一顿涮肉——这是“美食荒漠”在寒冬送给我们的礼物。

▲ 图 / 电视剧《云南虫谷》
刚才说到烤鸭,我还想说说近几年成燎原之势的北京菜馆。除去上面提到的老几位,劲松桥十字路口东北角的聚德楼饭庄,哎都不想告诉你们。从前年国庆节偶然发现,到上个礼拜五,近两年时间里我跟各路亲朋好友吃过也有几十次了,一道酱爆肉丁从不失手,而且两年没涨价。大拇指指甲盖见方的肉丁,应该是炸过,外皮焦脆,口感略甜,据说是原创菜。原创不原创不知道,出品稳定就是真功夫。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什么可以称作北京美食呢?也有,不过,都是小吃。烤白薯,糖葫芦,那些大冬天喝着风蹲墙根儿底下才能吃出境界的,上不得台面,但是我从小就吃的。烤白薯一定是马路边上的大炉子,无照摊贩烤的,拉着粘儿的,连我们家猫都喜欢。

▲ 图 / 电影《大事件》
至于稻香村,我不怎么爱吃,但每次我说不太喜欢稻香村,身边的其他普通北京市民就铺天盖地批判我,搞得我简直像是北京的叛徒。
对稻香村的偏见,来自于以前过年时不知道谁送的点心匣子。但朋友们都批判我了,说我需要与时俱进,现在稻香村很可,细致了很多,也不那么甜。我是非常乐于在这些事儿上被改变观点的。毕竟人家进步了你看不见,只能说明你不进步。
后来,我就在朋友圈问稻香村什么好吃,票数最高的也买了尝了,还行,可是非要说有多好吧……那还是北京的叛徒。当时,票数排名靠前的都有:枣花酥、蜂蜜蛋糕、雪花酥、云腿月饼、玫瑰细沙月饼、白萨其马、元宵、牛舌饼、糖火烧。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尝尝——毕竟,在北京,挤兑全聚德,北京人民大概率不太会急眼,但挤兑稻香村,那就不一样了。

▲ 枣花酥。图 / 网络
排队
在北京,吃饭排大队这事儿,并不是这些年网红餐厅兴起才有的。北京的饭馆好像有个习惯,就是跟风,也叫同质化竞争,哪个饭馆火了,就有很多效仿者,类似的餐厅一开一堆,一股风潮就这么开始了,风潮中,也总有那么几家风口浪尖上的,门口天天排大队。
大概在两千年代初期,北京特别流行水煮鱼,开了很多家,几乎可以算是年度流行菜。当时,有名的店包括沸腾鱼乡、渝信、红京鱼,甚至都有各自的拥趸。到底是沸腾鱼更好吃还是红京鱼更好吃,能打起来。跟豆腐脑甜党、咸党之争性质类似。
那时候,春秀路上沸腾鱼乡总店,天天人满为患。记忆里那家店有个巨大的后院,等位的都在后院集中。什么叫年轻啊,就是吃到嘴都麻了,那一礼拜也得吃两顿。
客观地说,沸腾鱼乡还是挺好吃的。就是很给劲。那时候常吃,也是因为年轻,经得住麻和辣,但流行这种事儿就是,流行着流行着,那阵风就过去了。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北京的交通成本太高了。现在日常吃饭聚会,都选离家近的,除非关系特别好,才会在非高峰时间跑一趟。不然不去。当然,另一个原因是年纪大了,身体没那么耐造了。
关于排队吃饭这件事,真是和年龄有关。
年轻人可能愿意去排队,因为他们的生命里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等得起。他吃了一个这样的餐厅,那种满足感可以覆盖付出的时间成本。可是对我来说,吃什么也覆盖不了这个时间成本。真的是,年轻时候说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不行,人生的进度条都过半了呀,有那么多正经事的优先级都排在吃前面,读几页书不好吗,看看花、树,甚至看看天上的流云,想象它是个什么形状是像小狗还是飞船,这些都比排队等吃饭有意义有价值。
现在,能让我排队的,都是一些极特殊的情况,比如,重要的日子请家里的老人吃饭。
今年过年时候请公公吃饭,选了东三环双井的拾久,11:00开餐,我10:08分到了拿号,前面已经排了10桌。服务员说有9:00就过来拿号的。这家店自打开业就长年累月地排队。没点儿决心就吃不上那种程度。至于为什么排队,因为它能做到这些年每次去吃,都出品稳定不失水准,口味上绝不输给大董,价格可比大董亲民多了。
最爱他们家小点心。人民总说北京小吃太糙、难吃,建议去它家尝尝,豌豆黄、驴打滚、芸豆糕,特别精致,口感细腻也不甜。鱼头也不错。就是随便点不踩雷。但也有一说一,每次去吃,菜品质量,我是服气的,但服务啊什么的总会有被我挑出毛病的。
另一种能让我心甘情愿排队的,是最好的朋友就想吃那一口。
最近的一次等位,是今年春天,闺蜜火了心想吃牡丹园那边一个广州顺德菜馆。它就叫“广州顺德菜馆”。就好像一个猫它就叫猫。菜单就一个塑封的三折页——马龙得过冠军的那单子都比他们家菜单长。
那天,大风地里,我们等了快俩钟头。至于那顿饭,吃完后,火了心想吃的闺蜜评价:这热评榜北京第一名的粤菜馆确实有点夸张了,但身处美食荒漠吧,但凡您馋广东家常菜了,倒是算得上是个打牙祭的可去之处。
在这里跑题吐槽一下某点评网站上的美食点评,怎么净是发自拍的,不是点评美食么?发自拍是怎么回事儿呢?
再说回排队吃饭,我现在的态度是,没有一顿饭是值得排队的,如果是为了我自己,一秒钟我都不乐意等。但如果哪天我真去排队吃饭了,那都是为了极为重要的人(幸亏没几个)。

▲ 北京某家早餐店的排队盛况。图/《早餐中国》
海底捞最大的缺点是服务太热情
说到排队,我自然地想起了海底捞。
火锅是北京餐饮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类,海底捞曾经是我认为的火锅界的第一名。直到六七年前,我还是这么认为的。
首先,它肯定不难吃,再加上服务太好了太热乎了。曾经它位于请客聚会的首选梯队。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公司同事姑娘过生日,我们将近十个人去吃的,除了寿星之外,其余每人出了大概八十块钱,给那姑娘买了一双她特别喜欢的鞋。那天,吃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拿出来给她,一个惊喜啊。那种发自内心的欢乐的气氛,跟海底捞大呼小叫的环境无比契合。服务员上下翻飞耍一根面,曾经我也认为那很有趣。
但后来,在北京,海底捞好像就没那么招人喜欢了,我自己最大的感觉就是——渐渐地觉得海底捞太不让人清静了。
关于海底捞的服务,我有一个“瞎想”,不一定对——就是最早以前,人民没像现在这个富裕程度,大家出来吃饭,还是想要一种被服务员围绕的感觉,包括请客也是,有服务,请客的人也会觉得有面子。那么海底捞那种服务,它可能是满足了大多数人的这种需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出来吃饭,说事儿聊天是刚需,就不愿意被过多打扰,你服务员在食客面前来回穿梭,一会儿过来问问给您添点水么,一会儿给您换骨碟,桌上有一张废纸都要冲过来立刻收走……食客不理人家不合适,没礼貌,可是刚刚讲到私密的、重要的事儿,就被打断了。一顿饭,这么被打断三回五回,那心情,你想想?
过犹不及,海底捞就是太过了。为什么现在的海底捞已经几乎不是我们聚会吃饭的选项了,没法给顾客一个“得说话儿”的环境。这也是海底捞始终让我无比佩服也无比疑惑的一点——它是怎么做到让每个服务员都时时刻刻打了鸡血一样?这是普通人类能做到的吗?
后来,有媒体报道说,海底捞餐厅的头顶上全是摄像头,会时刻监控服务员的服务,笑没笑,有没有让顾客自己倒水,这听上去就有点令人惊悚了,也让人不由得琢磨,那些追求极致的“变态服务”的背后,真相恐怕也都是残酷的。
至于什么是舒服的服务?我理解就是,“不叫你就别理我、叫你别不理我”,说起来就这么简单,但可能实施起来,如何拿捏这个度,也不是很容易。比如说,盛汤或者打包,我说我自己来,你就别非不让,非要替我来。“自己来”的潜台词就是,我们要说话,不太想旁人听见请理解。我都明确表示了,您就从了我吧。

▲ 图/《甲方乙方》
甜
在传统印象中,大家都会觉得南方人更爱吃甜,但事实上,北方人要真吃起甜来,那也是不遑多让的。
我喜欢吃甜食(包括炒菜也喜欢略偏甜的),跟小时候有关系。
我出生于1969年年底,小时候家里没钱啊,吃不到什么好吃的。大概五六岁吧,有一天我发现,我姥爷怹买了些吃食,好像是绿豆糕,似乎有八块之多,藏在他自己放衣服的小柜子里,旁边就是袜子,包括我姥姥在内的人,都不知道。
这个秘密被我发现之后,我就去跟我妈说,表达了很想吃的意愿。那天姥爷没在家。我妈说,“吃吧吃吧!”我就拿了一块吃了。哇,绿豆糕真好吃啊,这么好吃啊!可是我妈急了。她说,让我吃那是气话,没想到我居然这么没出息,还真吃了。记得那天晚上,姥爷和我妈、姥姥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也许就是因为小时候吃不到甜,长大了就特别爱吃甜啊。这种补偿心理,它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后来,印象深刻的一次吃甜,是十几岁时有一年中秋节。五姨提议说,姥爷一人儿做那么多饭太累了,不如啊每家都带些月饼回去,咱们来个月饼宴。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好,新奇又省事儿,全票通过。
聚会那天,三姨五姨舅舅和我们还有大姨家的表姐,每家都贡献了月饼。我记得,那些月饼装了三个大盘子,每个盘子都摞了三几层,摆在桌上,谁想吃什么馅儿吃什么馅儿,想吃多少吃多少。
一开始,大家还嘻嘻哈哈夸赞五姨出的好主意,没吃两块儿,我们小辈儿的表姐妹就开始四处踅摸咸菜,然后舅舅和我妈也开始挤兑五姨,说她出的馊主意,那么甜的东西,吃少了不解饱、吃多了烧心。姥爷则在一边儿嘿儿嘿儿地瞧着——大厨被轰出了厨房,他当然有权幸灾乐祸了。
那顿家宴最终怎么收场的我忘了。但我记住了月饼配咸菜,有如高山配流水、伯牙配子期。

▲ 稻香村的“自来红”月饼,很多北京爸妈永远的爱。图/网络
小时候喜欢的甜是恶狠狠的、满满的、丝毫不留余地的甜。但现在对甜品的最高评价反而是,不那么甜。就是不那么用力地、可劲儿地甜。如果用从一到一百来定义,以前喜欢的甜在九十多、恨不得一百那个位置,现在,一二十即可,三四十足够,五十到头儿,再甜就齁了,也不舒服。
关于甜,我个人的感受是,北京算不上匮乏,可选的类别也很多。
有时候突然上头,就想吃口甜的,家门口的好利来就行,北海道蛋糕来一块;紧挨着的宫门口馒头铺,来两块黄米凉糕也开心得紧。想吃点儿更好一点儿的,Venchi闻琦冰激凌,有GELATO也有巧克力,浓郁丝滑,我最爱的是榛子牛奶巧克力,冰激凌也最爱这个口味。比其他那些名头响亮的巧克力和冰激凌都好吃。
今日美术馆那边还有一家甜品店,出品的拿破仑独步北京(当然这是我的看法)。老板是在法国学过的。口感很细腻,也不会齁死的甜。店面不大,几张桌子,可以堂食,有咖啡。也可以外卖,就是送货费贵一点儿。送到家里,酥皮也不是一咬就酥,不会皮掉。每种都好吃。我尤其喜欢有巧克力的。
当然,对于健康饮食来说,甜,是伤天害理的存在。可有时候就是想吃点伤天害理的呀,辣的、炸的、甜的,垃圾食品最使人幸福——食物能提供的情绪价值,也是很重要的。

▲ 香草口味的拿破仑,酥皮又酥又脆。
一家餐厅的情绪价值
关于吃,另一种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是,餐厅的景观——这一点,北京也称不上匮乏。
有时候下馆子就是为了散心,吃得好不好往后排,有VIEW 有花园之类,就很加分。
举个例子。去年夏天,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天天跑医院折腾我爸,天天去急诊留观,天天见生离死别,特别累特别丧。有天下午终于得空,就去国贸80层吃了个下午茶。在那么高的地方,看着地面上显得比蟑螂大点儿的汽车,还有远处的山脊线,天空辽阔,白云疏朗,就感觉自己回到了人间。你说那下午茶点是多么了不得的美味吗,并没有,可是当时当日,它缓解了我积累许久的坏情绪。
马泉营的果园西餐厅,是每年蔷薇季我们的必打卡餐厅,那个园子,就像是莫奈的吉维尼花园。还有个猫,叫猫儿子,饭点在每桌之间逡巡。天气好的时候坐在户外,尤其舒服。

▲ 果园西餐厅
植物园里曹雪芹纪念馆旁边有个黄叶村酒家,初夏时节我们去过一次,傍晚去的,树荫下吃个红烧肉,夕阳给山镶了道金边,眼前的湖水波光鳞鳞,小院子里种满了月季,幽静深远,感觉在这么个地方,曹雪芹除了写《红楼梦》也没别的事儿可干了。

▲ 黄叶村酒家
顺义罗马湖十来年前还荒得很,如今湖的南岸一溜儿餐厅,有一家甲丁湖畔打边炉,好吃又美,坐在外面,可以湖水佐餐。北京不是多水的城市,湖景餐厅是稀罕的。
海淀稻香湖景酒店的岛上,有个维兰湖景餐厅,俄式西餐。菜品中规中矩,胜在临水,去年夏天去过一次,感觉四面八方的湖水都是我们的。
对我来说,所有的景观餐厅,就是提供了一部分大自然,还是大自然里美丽的那部分,因为这个价值,我愿意让渡一定的口味需求,差不多、不太难吃就可以。这是个人喜好,也有很多人肯定不乐意把钱虚花在这个地方。也特别理解。毕竟,吃饭又不是吃空气。
当然,有景观的餐厅大多也都不便宜,还是那句话——在平价美食领域,北京可能还是荒漠。
人
我喜欢的食客与餐厅的关系,不是那种“我吃我结账我走人”的关系。有些餐厅经常去,就跟厨师或者服务员认识了,一来二去越来越熟,彼此有种亲近在里头。
家附近的一家北京菜,有个服务员姑娘叫小白。自打这个店开业我们就认识了。因为我们两口子经常去吃,跟小白就特别熟。小白是那种永远向上、永远积极的样子。去年疫情期间,她从老家回来,也没有表现出颓唐之态。那是一个傍晚,我从地铁口经过,看见餐厅在门口摆了个熟食摊,再一看守着摊儿的是小白。那时候我们已经几个月没见了。当时就哇啦哇啦大呼小叫着戴着口罩拥抱了一下。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像餐饮业那样给我劫后余生的感觉。就是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小白也依然热情高涨,反而显得我特别挫败。
堂食的时候,我见过刁难服务员的、想占便宜不给钱的、得理不饶人的各种食客,有时候作为旁观者都气得不行,好像自己家妹子被欺负了。但小白都能得体化解。小白最让我佩服的是减肥,一努劲减下去50多斤。她休假回来,给我带过老家产的小果子,叫123。食客里有想给她介绍对象的,也有想挖她跳槽的,各种热闹。单小白一个人儿,都能单写一篇。
另一位因为吃饭认识的人,是一位寿司师傅。
双井家乐福对面,原来有家秋本寿司,后来搬到西大望路去了。他们店里有个寿司师傅,姓闫,精瘦利落,做得一手好寿司。
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坐吧台,闫师傅跟我说,“我看你不吃虾,是不爱吃还是什么?”当时我惊异于他的观察能力。要知道,一屋子二十多人的寿司都是他现做的,怎么还能有余力看出来我没吃虾呢。“我甲状腺有问题,医生不让我吃虾。”于是,闫师傅就给我换了个别的。等到我们第三次去的时候,进门就都互相点头打招呼,完全是老熟人那种感觉了。
他们搬到西大望路,我们就追到西大望路。我还碰见过新年前去吃饭给闫师傅送自己画的画儿的食客。后来闫师傅失踪了一年多。再吃到他的寿司是去年六月,临时去吃,发现闫师傅出现了。那种惊喜啊立刻先把微信都加上,这就跑不了了。闫师傅说去了南方,有意创业,然不擅此道,还是回北京了。
现在闫师傅在三里屯新开了一家店,我们还没有去过。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店,还是他主厨,总之希望生意兴隆。
总之,这些年,在北京吃了这么多顿饭,越来越觉得,“吃”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儿,味道很重要,但可能也只是其中最基础的一部分。即便北京是美食荒漠,但是也不耽误北京人民热爱生活,也不耽误荒漠里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人和回忆。
最近,关于“北京美食”的一条最新新闻是——北京要在5年之内成为“美食之都”,其实,关于一个地方是不是美食之都,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地方,中国也好外国也好,他的吃,哪怕街边的小饭馆也能做得挺好吃的,70分起步,那才能够得上美食之城。目前来看,北京可能还达不到。但这不还有5年吗,那就希望5年后,荒漠里能长出绿叶、开出花。

▲ 图/《饮食男女》
每人互动
你怎么看待北京美食?
文章经授权转载自人物(renwumag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