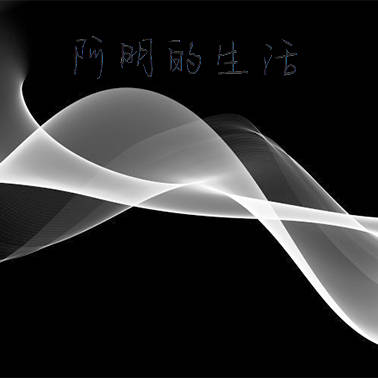我应该是馋了
横竖都觉着饿得慌
起身泡了一壶茶
这饭点没有由来
直勾勾盯着篮子里的两个萝卜
一个是我的上顿
另一个大抵是我的下顿……
。。。
过节总是要有点『节货』,如前几天老外们过的感恩节节货是火鸡,而我们前些日子的小雪节气,可称之为节货当属萝卜。
在半南不北的家乡,每到小雪时节,抢在霜冻前头把萝卜从地里挖出来。
萝卜好吃,却着实不耐冻。若是受了冻,刚出土的鲜嫩水灵就变成了『糠心』。
前些日子,赶着断崖式的降温,那些萝卜,应是还沾着泥土的新鲜劲,便陆续送上了餐桌。
旧时北方农村多有地窖,往地下挖个二三米,就可存放些不抗冻的吃食。有些地方将此专门称作『薯窖』,即专门用来存储地瓜红薯之类的粮食。
而萝卜,也常在里面借住,后来大概担心孩子掉下去爬不上来,便都从洞口盖上了石板。
除了放在地窖,更简单的储存是直接埋在沙堆里。农村盖房多用河沙,这种建筑原料的锁水效果堪比高档面膜,足以让一众化妆品汗颜。
扒坑埋土,随吃随掏。或许是因埋得太深太多,每年总会有被遗忘的萝卜在沙堆里发了芽,骄傲的开起了白花,似是在庆幸自己又捱过了一个冬季。
萝卜白菜,就是一冬。
北方严寒,往昔漫长的冬日菜蔬稀缺,大家大户的买白菜都是按车买。这顿白菜,上顿还是白菜,白菜炖粉条,白菜炖猪肉,更多的是白菜炖白菜。
一冬过去,脸都能吃出菜色。
而对萝卜,似乎就没有那么的抗拒。
大概也是因为萝卜养人,老一辈土话讲着『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大概萝卜也明白人们在这个季节里需要顺气降火。抛去食补,更主要的原因,大概在于萝卜无论煎炒烹炸,都各有风味,做菜做馅,味道都是美妙。
一根萝卜,就是一道菜。
除了寻常的烹炒,还有腌制。切片切条晒干腌制,甚至连叶子也能做成酱菜。咸菜界不可撼动的一哥芥菜疙瘩,似乎也是萝卜的近亲,只不过多了些倔强与野性。
『小雪腌菜,大雪腌肉』 腌菜,其实是把味觉封存,咸味里透出的模棱两可,是时间赋予菜蔬的味道。
儿时记忆里的咸菜总是够味,不似现在的小菜泡菜,几天就可出坛。
咸菜为了入味往往要闷在粗陶菜缸里好些个月,老一辈的咸菜,一定要够咸够下饭,往昔质朴,连咸菜都吃得节俭。
腌萝卜味道比芥菜疙瘩好上不少,生的脆爽,熟的咸香,还保留着萝卜原有的甜辣,做法粗糙质朴,却最让人心心念念。
萝卜除了当菜,也当水果。
大冷天,去澡堂子,一番搓洗,排板上拉八叉一躺,额头还透着汗,师傅递上切了十字口的青萝卜,辛辣里带着甜味。这会儿,那个嘎嘣脆,秒杀一切水果……
在老家时候,母亲会在年根时候炸一些丸子,通常是面团混着葱姜调料萝卜丝捏团下锅,材料与做法都颇为简单。刚炸出来的丸子外酥里嫩,美味可口,往昔油腻的年味最是让人怀念。
后来到了上海,家乡的炸丸子就不常见了,更多的是老人推着车在弄堂口做『油墩子』,不过是把丸子换成了饼子,虽是不同的做法,却满满的儿时味道。
关于萝卜,有着太多念想,飘零大叔,只能聊借回忆拉馋。天越来越冷,可念想越来越滚烫,大概是该归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