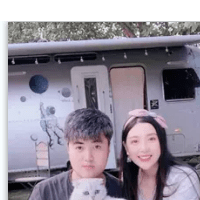那个女人喝多了,先是唱样板戏,唱着唱着,唱起了电影老歌,然后是很好听的家乡小曲,最后居然哭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颗滚落下来。

提起涮羊肉,北京人似乎特傲娇,因为他们有东来顺、西来顺什么的。其实上海也有吃涮羊肉的馆子,老字号中要数洪长兴名气最响,这是马连良在上海唱戏时一任性开起来的。马是回回,戏班里从琴师到跑龙套的都是回回。那会儿在上海跑码头,吃饭成了问题,马连良索性就开了一家,地方在连云路延安路口,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过几回,热气腾腾的共和锅,要排队!现在那里成了延中绿地。
洪长兴搬到南京东路广西路口,与燕云楼在同幢楼,云南南路延安路口也有一家。店经理叫默哈默德·宗礼,当然也是回族,我跟他熟,知道他本名叫马宗礼,名片上加了默哈默德的姓氏,外籍客人就找上门来,笃定吃喝了。马经理后来当选市政协常委。洪长兴的羊肉来路正,师傅切得也地道,这是羊肉好吃不好吃的关键。还有羊骨髓、羊腰、羊肝等,羊油做的葱油饼特别香脆,酥皮层层叠叠,别处吃不到。我不敢经常去,一不小心就要多吃多。
浙江中路上的南来顺也是一家老店。这一带还有几处清真饭店,不光羊肉鲜嫩肥腴,馕也烤得特别好。有一年我跟上海监狱管理局的干警押送犯人去新疆乌鲁齐木,为了一路上让犯人吃好睡好情绪稳定,监狱管理局的后勤人员特意到这里来采购了几大袋。馕的味道不对,新疆籍的犯人就不爱吃。
现在上海还有数不清的“小尾羊”、“小绵羊”,都是成规模的涮羊肉连锁店,谁说上海吃不到正宗的涮羊肉?在家吃也方便,电炉子插上电,锅底就起泡了,从超市买来的羊肉片排列整齐,一涮就行了,调料也有现成的。现在什么都方便,就怕没钱。

提起涮羊肉,想起一桩往事。
妈妈在世时有一个很要好的小姐妹,同一条弄堂,在我家对面,平时一起在生产组里绣羊毛衫。这个女人过去在百乐门里做过舞女,后来成了国民党军官的姨太太,解放军过长江后的第三天,这个上校军官带着大老婆奔香港了,把一个儿子和一个大老婆生的女儿扔给了她,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
几十年来,她靠一枚绣花针绣出了一家三口的吃喝,尴尬头上也会趁天黑未黑之际跑跑当铺。她居住的那套统厢房里有一堂红木家具,沉沉地坐着一丝底气,也仿佛守着一份微弱的希望,可是短短几年里就一件件地搬出去了。大破封资修的时期,红木家具贱如粪土,一具梳妆台雕饰极其精美,台上插着三面车边的花旗镜子,人面对照一点也不走样,才卖了六十元!
这个女人因为从前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据说还吸过一阵鸦片,身板单薄,脸颊瘦削,一幅弱不禁风的样子,但是鼻梁很挺,肤色也白,眼角没有一丝皱纹,满脸沧桑感,特别在她静静抽烟的时候。
她的酒瘾很大,每天要喝两顿白酒,她家里的茶杯没有一只不散发出浓浓的酒味,洗也洗不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她家里的筷子,象牙筷上镶嵌着闪闪发亮的罗钿,真是漂亮极了!以这样的筷子去挟红红的、圆溜溜的油氽果肉,一次没挟住,再挟一次,很有点情调呢。
大人叫她老三,因为她在家里的排行老三。我则叫她李家姆妈。

(照片与文章没有关系,选取自网络老照片)
李家姆妈对吃是讲究的,一到冬天就开始筹划吃涮羊肉了。今天的青年人听到“筹划”两字或许会笑,但在当时确实要群策群力的筹划,在猪肉需凭票供应的情况下,羊肉在菜场里几乎看不到,就得到郊县或外省去找。
北风紧了,羊肉还没买到;屋檐下挂起了冰凌,羊肉还是没买到;下雪了,密密麻麻的雪片飘到头发上,眉毛上,粘住了不肯融化,我再去她家里。哦,厨房里说说笑笑的好不热闹,七八条人影在灯火下晃动,女儿在升火锅,儿子在拌花生酱和腐乳,还有不知从何处弄来的韭菜花,气味刺鼻。我心中一喜:羊肉一定买到了。李家姆妈在里面的房间里找酒杯,大大小小摆了一桌子。
“再过一小时来吃涮羊肉,一定要把你妈拖过来啊。”她欢天喜地地说,简直是有点老天真了。今天,这张笑脸还清晰可忆,眉宇间真有一丝凄凉冻着。
涮羊肉太好吃了,菠菜、粉丝还有冻豆腐也都很好吃,只是火力不足,底汤再沸常常要等一会时间,七、八双筷子一起开涮,小小火锅怎么经受得起。吃着喝着,看一眼窗外大雪飘飘,额头上就止不住渗出汗来,我的脸很烫很烫。
李家姆妈的儿子初中毕业,正在等待分配,根据这一届的政策,大概率要去农村修地球,所以他情绪低落,收拾桌椅的动作也很粗糙。她女儿在一家街道工厂做,朋友谈了好几个,一个也没成功。她很懂得打扮,一件大红的绒线衫,领口扎了一条白绸巾,幽幽地散发着蛤蜊壳一般的光泽,乌黑的头发披在肩上,喝了点酒后更加美丽。这个时候我已经略微知道哪种女人漂亮了。
很温暖的一夜。

(老街风情,陈刚毅摄)
偏偏,那个女人喝多了,先是唱样板戏,唱着唱着,唱起了电影老歌,然后是很好听的家乡小曲,最后居然哭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颗滚落下来。妈妈劝她,她不听,有点撒娇的样子。儿子放下筷子,一筹莫展地看着她,女儿平时跟娘话就不多,草草地扒了半碗饭,就躲进自己的小屋不出来了。
一锅混浊的汤噗噗地沸腾着,不断释放诱人的香气。
绿的菠菜,红的羊肉,白的豆腐……空的酒瓶。
最终,我还是拉着妈妈的衣角回家了。妈妈手里挟着一包李家姆妈来不及绣完的羊毛衫。雪停了,风也息了,地上的积雪很厚,也很白,我迟疑了一下,还是踩了上去,一个很深的脚印。冷冷的月光叫我想起李家姆妈的脸。

沈嘉禄,《新民周刊》主笔、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作品曾获1990年《萌芽》文学奖,1994年《广州文艺》奖,1996年《山花》奖,1991年、1996年《上海文学》文学奖。2004年出版《时尚老家具》和《寻找老家具》,展现经典老家具的不朽魅力,引领读者在古典与时尚之间穿梭往返,开启了西洋老家具的文化鉴赏之窗,成为那个时代喜欢西洋老家具人们的必读之书。他也爱好收藏,玩陶瓷与家具,但他更愿意被人当做一位美食家,以一名上海老饕自居。

沈嘉禄绘画作品

沈嘉禄绘画作品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图文均由作者提供
特别鸣谢老有上海味道公微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