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到来,仿佛天然就和“吃”有关。
伴随着春回大地,万物重生,早春的蔬菜纷纷伸了伸懒腰,从地底探出头来。春韭、春笋、香椿芽、嫩蒿、荠菜、榆叶、萝卜……鲜灵的小春菜们,也如那五彩缤纷的春光,卷入面皮,被人类张口咬住。
“咬春”,生动中带点急迫,是属于吃货的词。实际上,一年四季,又有哪一天不是食物的舞台呢?是食物,让日子实实在在地被充满、被治愈。
身边爱读日本文学的人多,爱吃日本料理的更多。像我这般常被日本文学作品勾起食欲,嘴馋天妇罗、鳗鱼饭、寿司、刺身,在深夜实在受不了文字诱惑而从冰箱里拿出一罐朝日啤酒的家伙,怕是也不少吧。
待到吃多读多之后,才开始慢慢意识到:文字可以影响我们的饮食,饮食同样会造就一个人的文风,同样的食物在不同人口中的迥异感觉和相关描述,还能帮助我们走进作家的世界。

夏目漱石

芥川龙之介

泉镜花

种田山头火
饕餮或谨慎的他们
旧时的作家似乎大多拥有一副脆弱的肠胃,这一事实与上世纪初大部分传染病未被根除,生命如风中烛火般易于熄灭的情况,以及日本民族根性中的“物哀”审美相结合,塑造出了众多日本作家独特的饮食习惯与人生观点。
日本近代文坛巨擘夏目漱石长期为精神衰弱所折磨,因而有了神经性消化不良的毛病。他在英国留学期间长期水土不服、饮食不适,回日本后可以说是报复性地大吃特吃。他喜欢的要么是西餐中偏油腻的食物,要么是鳗鱼饭、寿喜烧等偏“重口味”的日料,还尤其嗜好例如羊羹这样的甜品,总之都是些消化不良患者不该多吃的东西,因此受到夫人的严格管束。忍不住嘴馋的夏目漱石于是开始玩起了藏食物、躲猫猫、偷摸吃的游戏。
偷吃终究过不足瘾,夏目先生因而定期举办聚会,召集一些食欲旺盛的人(如一次要吃六块炸猪排的作家内田百闲),看他们吃,望梅止渴。
最终因胃溃疡导致胃出血去世的夏目漱石,生前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吃东西”,最终得到了一匙葡萄酒,先生就在品味着这点酒带来的最后希望时,溘然长逝。
与夏目漱石同为公费留学生的作家森鸥外,因为所读专业是细菌学,对吃有着过分苛求清洁的嫌疑。他的爱好是水煮蔬菜和水煮水果,梅子、杏子、水蜜桃、蜜瓜统统煮后再吃,他可怜的女儿跟着父亲用这样的食谱,以至于在亲戚家第一次吃到生的水蜜桃时“不禁为美味所惊叹”。
泉镜花和森鸥外一样,出于对疾病的恐惧在饮食方面极为谨慎,甚至到了对吃饭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步。肉类中他只吃鸡肉,吃面包不吃手指碰过的地方,泡茶要把茶叶煮沸再加盐才肯喝,如斯怪癖数不胜数。泉镜花的作品如《厌蝇记》《酸浆草》等都集中体现了他极端的洁癖,而他曾和谷崎润一郎这种急性子饕餮大胃王一起吃鸡肉火锅,结局就是谷崎没等鸡肉烫熟就急不可耐地捞出吃光,泉镜花一块也吃不到嘴里,最终忍无可忍发了脾气。
与夏目漱石和谷崎润一郎一样拥有旺盛食欲的是著名俳人正冈子规,此人食欲与其说旺盛不如说骇人,曾有一顿饭吃掉三只鸭子、三碗粥的光辉战绩,吃完满意赞叹道:
三鸭皆食尽,秋意好凄凉
正冈子规旺盛的食欲或许与他多病的身体有关,35岁即辞世且长期缠绵病榻的他对吃的执着正是对生存之乐的向往。他从临终前一年写到去世的作品《仰卧漫录》里面满满当当全是有关吃的内容。在病榻之上,他吃多了就吐,吐完继续吃,严重时一吃东西就腹痛如绞,但就算是吃止痛药也要继续。
正冈子规对食物的态度是珍惜而执着的,“一颗梅干吃两三次也不舍得丢掉,梅干的核不管怎么吸都有酸味,实在不舍得丢进垃圾桶”。
对食物有如斯眷恋,行文如有神助并具备强烈的感染力自然合情合理。后世文人远藤周作卧病之时读到正冈子规临终前的随笔集《病榻六尺》中关于炙烤鲣鱼的描写,不禁食指大动,病好后立刻如法炮制,却怎样也吃不出书中传递的美味,于是他恍然大悟,勾起他食欲的并非炙烤鲣鱼那有限的味道,而是正冈子规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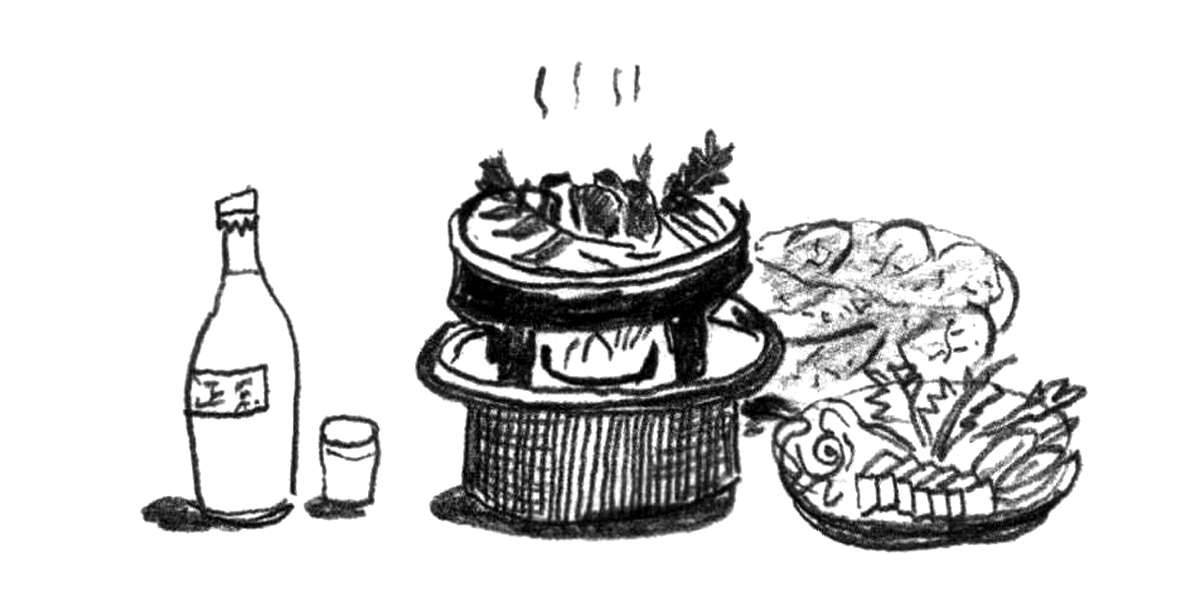
眷恋食物 如同眷恋生活
芥川龙之介同样是个脆弱敏感的人儿,他同时患有精神衰弱、胃酸过多和胃肠不适,病状与夏目漱石一般无二,但他对于食物的苛求敏感又酷似泉镜花。泉镜花曾在酒醉时吃下芥末章鱼,醒来安然无恙,知道自己吃了章鱼后却立刻腹痛难忍;不吃姜的芥川曾经大啖生姜蛋糕,被身边人提醒这个蛋糕加有姜后,身体如同被按下按钮,立刻开始腹泻。
很难分辨病痛对芥川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随着年岁的增加,芥川龙之介疯狂绝望的文风渐渐与其饮食习惯高度趋同。他对食色感到厌倦,乃至对进食行为产生了强烈的罪恶感,开始向往只靠吃罐头为生的简单生活。最终,他在35岁盛年选择与世界告别。不过,性格与文风都阴郁绝望的芥川也可以写出《蜜柑》这样充满人性温暖的短篇,想必在那暗色的外壳里,包裹着善良的内核吧。
川端康成的身体比芥川要好些,性情却同样晦暗,年轻时的川端甚至被评价为“遍身妖气”。他在饮食方面的癖好,一为爱吃白食,曾经坐着私家车到朋友家要饭团吃,二为食量极小而品位甚高。对美食的喜爱也许是川端对人生眷恋的唯一体现,其晚年作品《睡美人》与加西亚·马尔克斯更晚创作而名声更大的《苦妓回忆录》情节极似,均为一位老者与一个服下迷药沉沉睡去的年幼妓女共处的时光与思想活动,只是川端作品死气深重,有着强烈的将生之乐全数置之度外的感觉。也许是本就消极悲观又被安眠药之瘾折磨的川端已无法从包括美食在内的任何方面得到乐趣,他在72岁高龄选择赴死。
著名的童话作家宫泽贤治是个纯粹的素食主义者,他受《法华经》影响颇深,其世界观有很强的佛教倾向,不仅对人类饱含善意,还信奉大自然中一切生灵平等。这种心理倾向也使得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不是人类,甚至有雪童子这样拟人化的自然物化形象。
宫泽贤治生于富家却向往贫困,不仅只吃素食,而且是粗衣粝食,常见的食谱为萝卜干配冷饭或者酱油拌冷饭。这样缺乏蛋白质与油脂的吃法会让人对碳水的需求上升,宫泽贤治一天可以吃四合米(约720克,接近一斤半)。
那位“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毕生嗜好是殉情和自戕的太宰治先生,令人意外地很会吃也很爱吃,这实在有点突破想象,一个爱吃的人往往热爱生活,故而爱吃与自毁很少结伴出席,太宰算是个少见的例外。
不仅会吃爱吃,太宰还超能吃,曾经连续喝下六碗味噌汤,把井伏鳟二震惊得一塌糊涂。他喝酒如喝水,可以面不改色地干掉四斤清酒,还有一个人一顿吃掉一整条三文鱼的豪迈记录。太宰治虽然也是个严重的“神经质”,在饮食上却没有一点忌讳,曾和檀一雄散步闲聊时,从路边小贩处买了只毛蟹,边走边大口吞咽,须臾而尽。檀一雄还心有余悸地描述过太宰直接上手撕食一整只烤鸡的样子:“张大的嘴中可以看到太宰的金牙,头发散乱,撕裂鸡肉的模样如厉鬼”。
有这样的食量和这样的精神,让读者难以想象不说,还使人十分费解,大家只好称太宰是“健全的身体也有着殉情的精神”。
太宰治离世前一段时间最喜欢用鳗鱼肝下酒,殉情当晚与他同赴死的女读者山崎富荣还去买了分量空前多的鳗鱼肝,但是没给钱,店老板回忆道:“我说你今晚买得可真多啊,她回答今晚有事必须补充精力,然后第二天早上听说就死了,我也没收到钱,没办法,只能当做是奠仪了。”
太宰到死也没停歇旺盛的食欲,到死也没做个好人。
说了这么多,在吃东西方面,日本文人里我最欣赏的乃是行吟僧人、俳句名家种田山头火。这是一个食量很大,喜欢吃东西,也善于品尝食物真味并用文字表述出的妙人。身为一个游方僧,他过着漂泊无依行乞度日的日子,因此他对食物的爱与珍惜既出自天性,也因获取之难。其关于食物的俳句数量多且质量高,比如:
远方分手的人正煮着小菜,
洗着洗着萝卜也变白了。
影子幢幢,熬夜的我正在吃东西,
安静的冬季捕的活鲫鱼。
没东西吃时,万物在他眼中都是食物:
摘下经午后阵雨洗涤过的茄子,
蟋蟀啊,我只有明天要吃的米。
伸手可及无花果的忧愁,
汲取下得淅沥沥的雨水。
喝酒的山枯萎了,把所有的东西都煮成咸粥。
有吃有喝,杂草之雨。
草啊!被风吹的豆腐也冷了吧!
想喝的水发出声音。
食物俳句创作多了,弦外之音的运用逐渐熟谙,慢慢地,他的俳句虽然描写着食物,却有了味觉之外的含义。譬如在悼念亡母的俳句中,他言道:
把乌龙面当做祭品,
妈,我和你一起吃。
这位秉承“身无长物就是拥有世上一切”的快乐至上主义者虽然不时陷入虚无主义的厌世倾向,但在其大部分俳句,尤其是与食物有关的俳句中,闪耀着对生活的眷恋与珍惜。
饮食塑造文风,形成习惯,而文风与习惯在真实的生活本身面前又价值几何?若可眷恋食物如同眷恋生活,分享部分种田山头火的精神,是一件不错的事,毕竟我们短暂的人生,将会在读了很长时间的菜单中度过,想起那些数不清的餐盘,梦里都会笑出声来。太阳的光会烤熟面包,太阳的热气沸腾了麦酒。
这一切,就像夏目漱石临终前细细咂摸的那匙葡萄酒,充满希望,充满美好。
(配图选自“文人之舌”系列丛书,日本作家岚山光三郎著。)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佟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