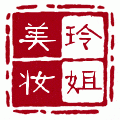本文转自:三联美食
『以豆子为主要原料的杂粮制品,是“山食农家小院”的特色。』
作者 / 丘濂
周磊在榆林经营的餐馆门口放了石磨和石碾子。刚从老高家返回榆林市区,我以为那纯粹是个摆设,因为高文停说过,这样工具在农村基本都是荒废,村民会送到专门的机器磨坊进行加工。
不想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真的在那里开始磨面了,原来是底下增加了电机来带动。周磊说,这样的好处是完全可以模拟人工的转速,一分钟稳定转九圈,不像钢磨,速度太快,香气在磨的时候就全部挥发了。
周磊捧了一把刚磨出来的杂粮面让我闻,里面有黑豆、高粱米、玉米和麦仁几种,其中黑豆还提前用铁锅炒成七分熟,为了让豆香更加释放。“这种杂粮面做成面食,吃到嘴里,香味都在。”当电机石磨闲下来的时候,也有住在附近的居民扛着成袋的粮食来这里借用机器磨面。周磊大手一挥让他们随便使用,“都知道这样磨出来的好吃”。
这家名叫“山食农家小院”的餐馆做的是农家风格的自助餐,36个品种里,有超过一半都是各种杂粮制品。榆林作为城市当然有十分高级的菜肴。翻看能找到的唯一一本榆林美食书籍、1994年出版的《榆林菜谱》,第一页竟然是海参和鱼翅来打头的海产,其他鸡鸭鱼肉各种菜式应有尽有,想必是为了突出榆林自古以来就是边塞重镇的富足殷实和饮食上的南北交融。
▲榆林大菜“拼三鲜”中的土豆片粉。这是“塞上饭庄”的名菜(于楚众 摄)
周磊觉得,这种以大菜、官府菜为线索的梳理方法,反而忽略了普通人的日常三餐,“其实一般陕北人吃得粗犷,比较原汁原味”。他原来在榆林市一家化工企业的食堂里,专门给领导班子做饭。他屡次受到称赞的,不是多么繁复的硬菜,而是一道普通不过的炒豆腐——榆林以普惠泉水做的黑豆豆腐出名。
周磊就找新鲜磨制的豆腐,放一点油来煎,再加酱油、糖、盐,出锅前放韭菜和小葱,就这么简单。他决定开餐馆后,提供的就是过去家里吃的那些东西。“每人26块钱随便吃,什么年龄层次的客人都有。但50多岁的妇女来到这里就特别情绪化,也不是大哭,就是眼角默默淌泪,因为能让她们回忆起老父亲、老母亲曾经做饭的味道。”
在这些杂粮制品中,和豆类相关的不少。豆子在陕北的饮食结构里是个奇特的存在。
有的豆子可以用来趁着鲜嫩时和豆荚一起炒着吃,或是发豆芽、磨豆腐,都算是素菜,还有的豆子可以做成酱,成为一种调料,但大部分豆子则都能担当主食里面的角色:豌豆可以做成“杂面”,也就是磨成粉之后再擀成面皮,但一定要加一种叫作沙蒿籽的东西增加筋度,才能擀出来和炕一样大、像纸一样薄的一片,再用刀做成切面;碗豆面还能做成“抿尖”,需要把面团在带有小孔的“抿尖床”上来回摩擦,擦出来的“抿尖”如同毛毛虫一般呈条状;以黑豆为主的杂粮面能做成另一种“擦尖”,“擦床”上是一条条细缝,“擦尖”像是一些不太规则的厚纸片;这样的杂粮面再加进有点黏性的软糜子,还能做成“窝窝壳壳”,也就是一般说的窝窝头。
图 / 摄图网
我曾经对杂粮制品这些奇奇怪怪的造型表示不理解,北京旅游学院教授面点制作的王美教授给了我答案:说到底,这都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想出的办法。小麦面粉的蛋白质吸水后可以形成面筋,弹性、韧性和延展性就有,能抻拉出各种形状。大多数杂粮就不同了,弄出个样子,就要赶紧下锅;杂粮面也无法做成松软暄弹的发面产品,因为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包裹住气体。这样一团死面放在蒸锅上难以蒸透,所以要在下面按一下凹进去,窝窝头就形成了。
豆面虽有特殊的豆香,但毕竟比不上白面那样细腻爽滑的口感。陕北人自有办法让它吃起来也能有滋有味。周磊特地恢复了陕北农家的调料盘文化。以前物质匮乏时,各家都只有过年才能杀猪宰羊。调料盘就是让平淡食物焕发魅力的神秘武器,也是各家婆姨比拼巧手的所在。
我在老高家也见过炕桌上的几种调料,但远不如周磊的餐馆里这般阵容华丽。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红色木质托盘,里面的12个黑瓷碗里五颜六色,暗藏着玄机,除了葱花和香菜,没有哪个是一句话能讲清楚的。他指了指那碗西红柿酱说:“这柿子必须自己种。要让它成熟到开裂,用手掰开里面都是沙瓤的,直接吃都发甜。
后半个夏天,我们在厨房里天天蒸柿子,放在玻璃瓶里存起来。柿子酱炒制的时候,锅里要再添花椒面、五香粉和老盐,放一夜入味了再吃,三天内要吃完。”那碗辣椒油也相当麻烦。“里面有三种辣椒,陕西凤翔的线椒要它的香,四川的二荆条要它的辣,贵州的灯笼椒图它肉厚。泼辣椒的油先要用葱根来炸香,油温降到180度再往辣椒面上浇。”
但最难得的还是那碗黑酱。它颜色是黑乎乎的,闻起来极其香醇和幽深,像要把人吸进去一般。做黑酱的原料就是豌豆。豌豆用石磨去皮之后,要在炉灶上蒸、炕头上闷,看到豆子起霉,就磨成细粉,加入老盐,放在大缸中。黑酱每年只能做一次,是因为它必须经过6月和7月份的高温暴晒。晒的时候缸子并不封口,要用木棍不断搅动,才能黑得通透。
周磊说,过去加工黑酱的办法是用油泼。会吃的人都用勺子去挖表面那层,因为下面的酱熟不了,是涩口的。他改良的办法还是要去“炸酱”,将花椒、桂皮、大料等七八种香料用菜籽油炒香,再把黑酱倒进去慢炸两个小时。“炸完的酱放起来冷藏,还会慢慢发酵,一个月左右,是最巅峰的食用时间。”周磊顺手拌了一碗豌豆面擦尖给我,加入了芝麻盐、西红柿酱和黑酱,又淋上一层辣椒油。质朴的农家餐食,也瞬间隆重起来。
电视节目《每日农经》
还有一道麻汤饭是周磊格外看重的。“小时候奶奶就给我做这个,现在用不上这个原料了,也就几乎绝迹。”周磊的馆子里每天上午和下午要各熬一锅。食客进了门,几乎每个人都要盛上一碗,在那里呼哧呼哧地喝着,脑门上顿时就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麻指的是小麻,过去陕北人吃植物油是靠压榨小麻籽得来的。
剩下的油渣还有点油星的残余,舍不得丢掉,就用它来煮稀饭,这就是麻汤饭的来源。如今没有了榨油的程序,周磊会从头来加工小麻籽。小麻籽先要炒熟,再在石磨上把它碾碎,放在锅里熬汤。“锅里水不能是冷水,冷水就把油给积住了,任凭大火也化不开。要温水加中火慢慢熬,半小时以后把渣滓捞出来放进纱布袋子里加点水,再揉搓挤压,直到油脂全部出来,小麻籽成了光壳壳。”漂着油花的汤里,继续把难煮的红豆、黄豆、老黑豆和菜豆放进去,又过半小时加土豆、小米、高粱和麦仁。临关火的时候,倒进去小麻油炒的花生碎和青菜,马上香气四溢。
那些熬汤剩下的小麻渣滓也不会浪费,周磊把它们放在大桶里发酵,当作有机肥料用在自己在城郊的菜园子里。
周磊对好的食材有一种痴迷,没事的时候就开着他卸掉后座的五菱宏光跑到乡下去收杂粮。他是子洲县苗家坪镇上的人,愿意优先考虑收购那里的作物,惠及乡民。“都多少沾亲带故,可我严格得很。每袋粮食上都写着谁家的,多少斤。今年发现有问题,明年就再也不会来了。”他觉得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赶上一种土话叫作“羊打脸”的高粱上市。“现在已经割下来放在外边了,冻上个几天,壳和肉分开,就比较好分离。”这种高粱种在坡子上,稀稀疏疏的产量不高,吃起来明显和一般高粱不一样,“特别滑糯,整个稀饭都是稠稠滑滑的”。每年冬至之后,麻汤饭里的高粱都会换成“羊打脸”这个品种,一下子又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