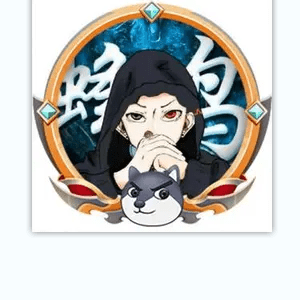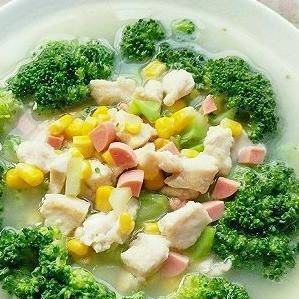我以前始终认为,好的吃食物一定得配上好的吃地儿,这就如同鹅肝一定要配红酒,刺身一定得配芥末一样,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带妹子去吃东西,更是得考究一下。因为好的妹对吃物一般是没怎么讲究的,别拿陈醋倒鱼翅里喂她就成,但是对于吃地儿却很是看重。妈的老娘穿着一身貂绒你带老娘挤破桌子吃沙县算怎么地?于是,我就极少流连于市井小店。自然是知道省府路附近有很多不错的吃店啊,可是一个人吃东西就如同一个人看电影,那无尽的落寞让人更不爽,于是常作罢。
直到这一次,一个好的姑娘约我,说咱们去省府路吃烤生蚝吧。于是受宠若惊的,揣上包就过去了。
福州是一个隐忍含蓄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容易出隐忍含蓄的吃店,更容易出隐忍含蓄的吃物。
穿过东街,拐进省府路,依然是稀攘的人群,却仿佛一下子就与世隔绝了,可是这样的与世隔绝却让人特别的感动。或者说,东街就如同姑娘家里堂皇的大堂,会客接亲置办一些宴会酒席,自然得母仪天下雍容华贵气质尽显,而省府路却仿佛姑娘家里的闺房,锁起门来,自然随性,少了一些面儿,多了一些里儿。
包括吃物们。
店是真的小,有装修,但装修的却不讲究,吸引人的是外面那一排排的生蚝带子扇贝们。姑娘说这家店便宜实惠东西也很好吃,于是就胡乱点了一堆。
先是小龙虾。如果说,普通的龙虾是西瓜,那小龙虾就是瓜子了。脑袋大,身子小,肉少。剥掉壳,吮一下,会吃的人,能吮到一口浓郁的黄膏,不会吃的人,也就只能舔到壳上那一股麻辣了。就如同吃瓜子似的,会吃的人,满口瓜肉,不会吃的人,满口咸。解决完脑袋,剩下的半个小拇指大的虾肉,就让人很纠结了。心急的人,囫囵吞枣的,整个丢进嘴里,咀嚼一阵,和着口水吞下。心细的人,慢慢地剥弄干净,炫耀似地看着手中的成果,却发现整盘虾都没了。龙虾的妙,在调料,整个地蒸好,倒上调配好的料们,就是饕餮了,小龙虾的妙,却是在吃的过程,一只一只的,有的时候被辣得口吐白沫的,手却停不住地剥着。
然后是生蚝。印象中第一次吃生蚝是在威海,那会儿去见女朋友,舟车劳顿的,一到地儿全身都软了。女朋友说那么长时间没见,走,带你去补补!一大盘生蚝端到面前,本来手脚就软,一下就更软了。于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人喂,再眼睁睁地感觉到丹田中冒起一股子的热气。于是很长的时间里,将生蚝当成了补药。可在这的生蚝,却是珍馐。烤前,倒上蒜泥,旺火,看着蒜和蚝水乳交融地翻滚跳动着,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起架上桌,还冒着热气,看着那么多的蒜泥,吃进口中居然没把蚝的味道给盖住。恰到好处的火候,也去掉了蚝本身带着的腥味.吃完蚝肉,看下壳里,还有一些乳白色的汤汁,想必是蚝和蒜交融后的遗落,他遗落了,我可不能遗落,全部吃下。
羊肉串,传统的记忆,大概是小学那会喏,校门口的一溜过去的跟打碟机似的摊位,蓬头垢面的摊主,破烂的蒲扇,飞舞的火星儿,细长的竹签儿,以及不知道什么动物什么地方的肉。曾经有一朋友吃那样的串儿,吃着吃着吃出根毛,大家都被那根毛给吸引住了,讨论了半天最后大家一致把这根毛定义为不是头发胡子睫毛外的其他毛,他也因此阴郁了很长时间。不仅他,我们也阴郁了。所以,对羊肉串一直不待见。直到去北方读大学,吃到了正宗的大块的肉嫩多汁的羊肉串,并一不小心吃掉了一个星期的伙食费,才对羊肉串改观。回福州后,吃的串儿门虽然肉都多,吃着也都像是那么回事儿,可感觉就是少了一点儿什么东西。这家店的羊肉串也是如此,要挑毛病,还真挑不出,却没有回味。可见一方水土养一方吃物,在北方吃蚝不也吃不出南方的味儿么。
如是。